书画艺术:王问草书七言古风卷
花鸟画艺术特色
鸟语花香作为大自然中美的对象,早在三代上古,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绘事之妙,亦相继寓兴于此,与诗人相为表里。据文献记载,六朝时的顾景秀,刘胤祖皆精于蝉雀,笔迹谨细,赋彩新丽,形象微妙,是花鸟画之蓓蕾初萌,至唐代薛稷的画稿,冯绍正的画鸡,姜皎的画鹰,均有名于时,大略以工笔设色的画法写生逼真,中唐以后,花鸟画正式独立成科,可以作为标志的便是边鸾,于锡,梁广等一大批花鸟画家的涌现。其中的边鸾的成就最高,他长于写生,画法工笔重彩,笔迹轻利,赋彩鲜明,形象生动逼真,中国花鸟画的传以及工草没色的技法,到边鸾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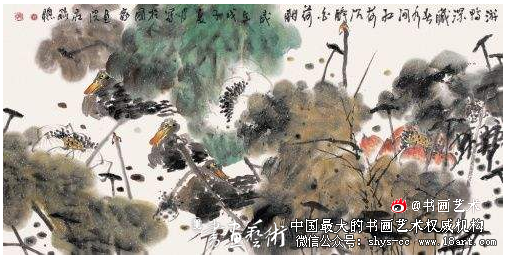
进入五代,以“黄徐异体”为旗帜,花鸟画一科臻于圆转成熟。当时西蜀的画坛,由刀光胤,滕昌礻右带去了唐代的传统技法,到了黄筌父子手里获得了进一步发扬光大,作风艳丽丰满,谚称黄家富贵,南唐的画坛,则以徐熙为代表,以落墨为格等江湖汀花野竹,水鸟渊鱼,意境清淡隽秀,谚称“徐熙野逸”,后世花鸟画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两大基本的传统技法之外的。
黄氏父子有“写生珍禽图”,“山鹧棘图”,存世,其作风,技法,大体而言先用细淡的墨线勾出物象的轮廓,然后再根据对象的不同质感在相应的轮廓内渲染色彩,所以达到高度的真实性和生动性。然而,徐熙及南唐诸家的真迹却无有流传,对于“徐熙野逸”的作风和技法无从考证。 北宋初年,由于二黄垄断了宫廷画院的权力,对徐熙的画派竭力加以排斥,“黄家富贵”的画体,遂得以成为画院中评定优劣去取的标准。因此,约有一百年的时间,院墙内外的不少画家都以黄体为格,亦步亦趋,陈陈相因,以求得画院中的一席立足之地,甚至连徐熙的儿子徐崇嗣,也不得不放弃了家传的落墨法,另创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的没骨法。

当然,这期间也有不为黄体所囿的画家,如赵昌专攻写,用没管法,虽仍属工笔没色的画体,但相比于黄家的富贵浓丽,则有轻清淡远的韵致,当时人评其设色之妙,旷代无双。又如易元吉,入万守山百里以窥獐猿动静游息之态、天性野逸之姿,作风稍粗放而摒去俗艳,论考推为徐熙后一人而己。 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对徐熙画派流连赞叹者大有人在,并从北宋中期开始,一股水墨写意而以枯木、竹石、梅兰为题材的文人画涌起,后来又加上菊花合称“四君子”,成为花鸟画科中一个特殊的门类,历千百年而不衰。
与此同时,宫廷画院的花鸟创作亦开始摆脱黄体的一家眷属。来自民间的崔白,崔悫兄弟,作为花鸟多在于水边沙外之趣,画风清淡疏通,放手铺张,势欲飞动,虽属工笔设色范畴,但明显已向粗放,清淡的格调倾斜,追求“孤标高致”,“野趣”,迎来了画院花鸟创作的全面繁荣。 皇帝宋徽宗赵佶,对画院的建设不遗余力,对花鸟画的提倡尤其着意。概括其对绘画艺术的要求,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注重写生追求客观的真实性,二是通过命题考试追求的含蓄性。在其影响下当时画院的花鸟画创作呈现出形象逼真、意境生动的特色。比之二黄,有了长足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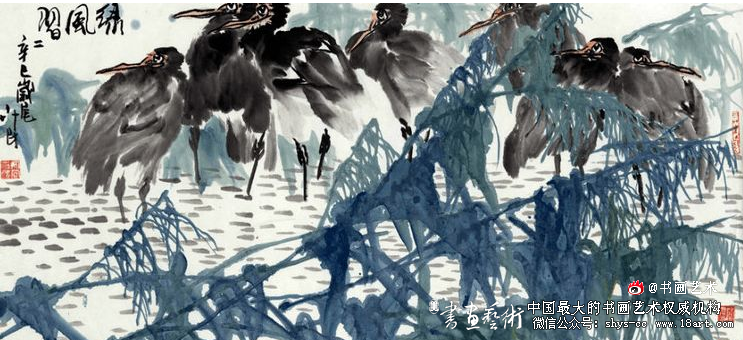
其画风有两种,一种用浓郁的重彩画成,源于黄体,另一种用清淡的水墨画成,源于徐熙。其作风又有两种:一种工笔细勾淡染,与院体无异,只是变色为墨而另一种粗笔,连勾带染,点垛兼施,但依然恪守形象的真实性。 南宋宫廷画院的花鸟,在艺木思想上乃画风形态上,无不受赵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中不少著名的画家如李安忠、李迪等,本来就是宣和画院的画师。此外如林椿,吴炳等均为一时高手从具体画法而论,南宋画院虽与宣和画院一脉相承,但宣和画院多为大幅画创作,至南宋初期的李迪犹然,而南宋画院多为斗方,团扇形制的小幅面创作。因此,就风意境而论,前者有辉煌壮丽之观,后者清新腕约之致。 除工笔设色的一路之外,当时的禅林之中亦以花鸟画画坛化为顿悟的机缘,画法用水墨大写意,极其恣肆奔放,完全脱略形似以神韵为尚,其意境又在徐熙落墨法之外。
先在画院后又入禅林的梁楷所作多取远景,牧溪则多写近景;梁楷擅于用笔而性格较为刚斫,牧溪擅于用墨而性格稍趋柔和,这一路画风后来东传日本,对日本画坛影响至为深远。文人士大夫中,除枯木,竹石,梅兰外,如杨无咎,赵孟坚等,还兼能画水墨水嫌体,杂卉画法用工笔双勾,而有别于其梅,兰,竹的点垛,但气韵的清高幽隽则是无有二致的。 元代花鸟,由于赵孟 的竭力反对“近世”,认为“用笔纤细,赋色浓郁”的画体,“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所以工笔设色的作风,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仅钱选所作,精工而不失土气于赵昌,林椿之后别开生面,任仁发的画整,便明显板了一些,远不及宋人的精采生动。与此同时,梁楷,牧溪水墨粗放的一路,同样不合元人鉴赏的心目,被认为粗恶无古法,诚非能雅玩。他们所推崇的是赵孟坚工整清淡的墨花一路,同时受水墨四君子画的影响,开创出墨花雅玩禽的风气,既对院体花鸟作了大跨度的改造,又扩大了文人画在花鸟画领域的表现题材,为明代以后文人花鸟的兴起,起到了先声的铺垫作用。

元代墨花墨禽画家中,陈琳,王渊为职业画工,他们的画法纯出院体,严谨而又写实,稳健的骨体和华美的铺陈,反映出功力的精湛,但以墨易色的渲染,所引起的情调和意境,却是淡雅而宁静的,另一位张中则为文人画家,其画风一变院体的刻划严谨,而以松秀,率意的笔致点染挥洒,兼工带写,更洋溢着生动潇洒的野逸之趣,此外,还有边鲁,盛昌年等,画法不出两者之外。 进入明代以后,宫廷院体花鸟一度复兴,并由工笔粗笔转化,如边文进全学“黄家富贵”,双勾填色,稍嫌板刻艳俗,林良长于水墨,虽用草粗劲,气豪放而不失法度的森严,与文人有别,吕犯则有重彩的,也有水墨清淡的,凡重彩者,比之边景昭较活泼,淡淡者比林良又较文静,所以在宫中影响最大,学者甚众。另有金门侍御孙隆,常与宣宗朱瞻基一起探讨画艺,两人的作风有所相似,而以孙隆的成就为高。他的画法不用笔线勾勒,而用颜色直接点染出来,充分利用不同色阶的自然渗化和衔接,来表现对象水淋淋的质感,具有现代水彩画的效果;其形象的刻划,不求细节的真,往往以虚为实,笔简意足,与院体迥异。后来文人花鸟画的发展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变色为墨的改造而成。 明代中叶,文人花鸟汲取张中,林良,孙隆诸家之长,墨花齐放,逸兴纷飞。如沈周无论勾花点叶刷羽,松秀处近张中,森严处近林良,烂熳处近孙隆,唐演清刚的笔墨则以近于林良者为多,但清丽的诗情却是他的独擅,非林良所能梦见。至陈淳后出,更以水墨大写画法开宗之派,与后来的徐渭并称“白阳青藤”。他善于运用草书飞白的笔势,水晕墨章的墨彩来表现花卉离披纷杂,疏斜历落的情致和态势,其气格是奔放的,品格是秀丽的。再后的周之冕以勾花点叶著称于画史。 徐渭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怪杰,他的水墨大写意花鸟虽与陈淳并称,但二人的画格迥然有别。陈淳画生动而不失文静蕴藉,属于传统文人当中和美的范畴,徐谓的笔墨则恣肆汪洋,喷放着一股磅礴飞动的激情和力量,借以发泄其满腔的怨愤,正所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传统文人画的蕴籍,文雅,宁静,文质彬彬,同他是无缘的。因此,其创造性虽大,但从艺术性的角度,尚有待进一步的提炼升华。

徐渭之外,陈洪绶的工笔没色画体在花鸟画苑史上也作出了迈绝前人的创造性贡献。其特点是通过夸张变形的形象,使之涵有图案化的装饰趣味,从而使笔墨线描和色彩晕染也从以往的造型功能中解散出来,取得了一种相独立的审美价值,高古宁谧的意境,为雅俗所共赏。他也有水墨的画体,其画品的高古与设色之作是完全一致的。 八大山以泪和墨,所常常描绘的题材有菏花鱼鸟,芦雁汀凫芭蕉松石等等,浩阔清空的境界,怪诞夸张的形象,奇特冷峻的表情,是被扭曲的心灵的其实写照,大片的空白处理,计白当墨,虚实相生,足以使无画处皆成妙境。他的笔墨,主要是从林良,徐渭中脱胎而来,但是林,徐的奔放,狂肆躁动,却被凝冻在点滴如冰的苍凉、悲怆和含蓄之中,显得特别的圆浑,蕴籍。
笔墨习性的这一改变,标志着水墨写意的花鸟画派真正进入了文人画的审美范畴,八大山人和石涛代表着这一画派的最高成就。石涛花卉画法虽也属大写意,但所抒发的情调却无亡国后的悲凉索寞,丰腴俊爽的笔墨,清新奔放的才华,天真烂漫的氛围,洋溢着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与八大的幻心境,形成显成的对照。另一位遗民画家寿平,则以工细清丽的笔调,开创了宋元明以来所不曾有的写生风格,是陈洪之后又一浓于文人书卷气息的工笔设色画派,没骨渍染逸气横溢,脱尽院体的富贵萎靡之习。

其特点有三:一是以极端的形似逼真乃称为花传神;二是色彩的渲染淡雅纤丽,精妙绝伦,三是笔法的运用妩媚刚劲,婀娜遒逸,评者譬为“天侧化人”,一时学者甚众,并传入宫廷画院,如蒋廷锡,邹一桂等均传其衣钵,世称“写生正派”。 乾隆之际,宫廷花鸟除写生正派的板刻艳俗之外,另有以郎世宁为代表的“中西合壁”,画体系用西画的观念、方法,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来作画,形象刻划几同照像摄影,但神采全无,所以“虽不亦匠,不入画品”。倒是宫外的扬州画坛,花鸟画创作盛极一时,明显压倒了山水、人物的势头。 晚清花鸟画坛,海派的赵之谦、四任、虚谷、吴昌硕均称巨擘,其共同的特点是讲究金石书法的。用笔挥洒浓丽清新的色彩,描写喜庆吉祥的题材,作为中国画商品化的最佳形式,提供了传统绘画向近现代转轨的成功契机。其中而又灏瀚,开启了近现代花鸟画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