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赏析:中国李可染书画艺术院理事杨旭尧——“李家山水”经典传承
关于《书法真诠》的批评(下)
关于《书法真诠》的批评(上)
《书法真诠》批评范型滞后的最后一个表现,在于它的批评话语太封闭了,知识背景呈现出不该有的单向度———只见传统承继而不见新的横向移植(即对西方现代文化知识的及时吸纳与化用)。
在西方学术话语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当然无法(也不应该)要求国人的书法批评走出单纯的传统学术话语体系。但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西方学术话语已被国内众多领域加以广泛吸纳、运用之际,我们的书法批评就不该对新的学术话语视而不见,继续将自己封闭在传统学术话语范围之内。
因这样,除了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是地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也许,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立场者从来都是与“时代”相隔膜的。不然,何以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书法理论界和书法批评界,居然还有部分学者极力主张进行书法研究和书法批评只能运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其实,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书法研究与书法批评即因引进西方学术话语而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至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美学之崛起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学术话语当然具有民族性,但同时它还具有超越民族的世界性,在一定程度上“通约”所有民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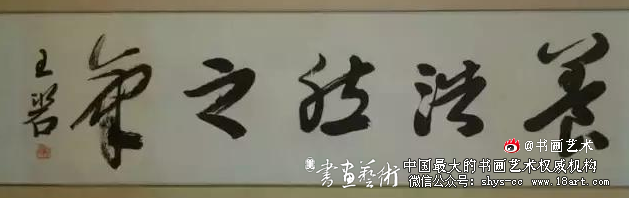
即是说,西方学术话语可以为我们中华民族所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也可以为西方民族所用,只不过因综合国力等因素影响,这种双向互用目前存在巨大的规模差距而已。对同样一个书法现象或书法批评对象来说,运用(或兼用)与不运用(或不兼用)西方学术话语加以解说,那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运用(或兼用)之,则可帮助我们达到“透彻化”的高度;不运用(或不兼用)的话,就永远只能停留于印象式、平面化的水准,那结论常常也不能让读者心悦诚服、有效接受。这里不妨就《书法真诠》“恶札”章中的批评对象之一“媚世者”加以具体说明。
《书法真诠》所批评的“媚世”现象,用西方学术话语来观照,就是创作者没有风格意识与风格化作品的现象。有人认为,在西方学术界,最先提出风格问题的是希腊的狄米椎耶斯。其后,到18世纪,又由法国作家布封提出“风格即人”的思想。他说:“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
他进而又说:“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布封“风格即人”思想问世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相继受到黑格尔、马克思、李卜克内西与威克纳格等人的极力推崇。
在“风格即人”的西方学术话语面前,《书法真诠》所批评的“媚世”现象的症结一下就暴露出来:仅止于“临仿各帖”,不见自己的“真面目”,说明其“书法创作”(姑作如此称谓)尚未体现出书写者的鲜明个性。而鲜明的个性又是真正的书法创作所不可或缺的。
由此,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风格意识的书法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没有风格化的书法作品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如果凭赖风格论这一西方学术话语做理论后盾,谁还会对我们的结论表示怀疑呢?
当然,《书法真诠》“恶札”章在封闭性批评话语中提出的“字乃美术”之主张,我们还是认为完全可取的。“字乃美术”的主张,今天看来已极为寻常。但在20世纪初叶(即《书法真诠》成书期间),它的提出却显得卓尔不群、难能可贵。因为当时出于强国之虑,国人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都积极实行现代转型,依西方文化模式改造、重组中国传统文化。其遵循的原则是:凡西方文化中有的,我们都要拥有;凡西方文化中没有的,我们都要一律革除。这样,作为中国文化特有之书法,便自然而然地被排斥于“美术”(或“艺术”)之外。绝大多数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不再把书法视为“美术”(或“艺术”)之一种。
从一般规律来看,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总是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有了繁荣的创作才会有相应繁荣的批评,反之亦然。对《书法真诠》来说,其批评范型的滞后,作者主观因素当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当时书法创作整体滞后于其他艺术创作。正是这样滞后的现实因素,最终决定了当时书法批评范型不得不处于滞后状态。如前所述,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再把书法视为一种“美术”(或“艺术”)而远离书法创作,那还如何指望书法创作紧跟时代、走向现代转型呢?不仅如此,就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段书法复兴期,我们的书法批评仍然不见大的作为,更谈不上批评范型的现代转捩了。书法批评范型整体实现现代转捩,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所以,笔者指出《书法真诠》“恶札”章批评范型的滞后,并非为了全盘否定《书法真诠》的批评实践,只是意在揭示一个大家习焉不察的客观事实:书法批评是难的,书法批评范型的现代转捩更难,难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与近百年的等待。(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