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麗和和花耀高级珠宝系列:大地之耀
审美杂谈
拉斐尔画了许多“圣母像”,他表示:我的圣母不是用现实生活的一个美女为模特儿的,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众多美女为模特儿的,萃众美于一身而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圣女。毕加索画了一幅《阿威农的少女》,观者大惊失色,认为世界上哪里有这么丑的女人!毕加索回答:这不是几个女人,而是一幅画!中国古代的经典,唐宋画中的形象,无论人物还是山水、花鸟,“不知人间何处有此景”,比生活真实更美;明清画中的形象,无论人物、山水、花鸟,“以径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远不如生活真实美,情况与此类似。即形象的艺术美与生活美可以迥然相反,美的生活形象可以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而且比生活美更美,这是正常的“审美”。丑的生活形象也可以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而且比生活丑更丑,这就是“审丑”——在外国叫“变形”,在中国类似“不求形似”的“写意”。抛开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对于艺术美中心的不同不论,古典美以形象美为中心,美的形式服从并服务于美的内容即形象的创造;现代美以形式美为中心,在中国以笔墨美为中心,“丑”的形象即内容服从并服务于美的形式即笔墨的创造。它更证明了一点,即艺术形象美的创造,是需要与生活真实拉开距离的,写实的艺术形象,向比生活美更美的方向拉开,与生活美的标准相一致而成为生活美的理想;不写实的艺术形象,向比生活美更不美、比生活丑更丑的方向拉开,与生活美的标准相反对、与生活丑的标准相一致而成为生活美的反思、生活丑的针砭。生活美必须通过“审”才能成为艺术美并高于生活美;生活丑也必须通过“审”才能成为虽然不如生活美、丑于生活丑而“丑得如此之美”的艺术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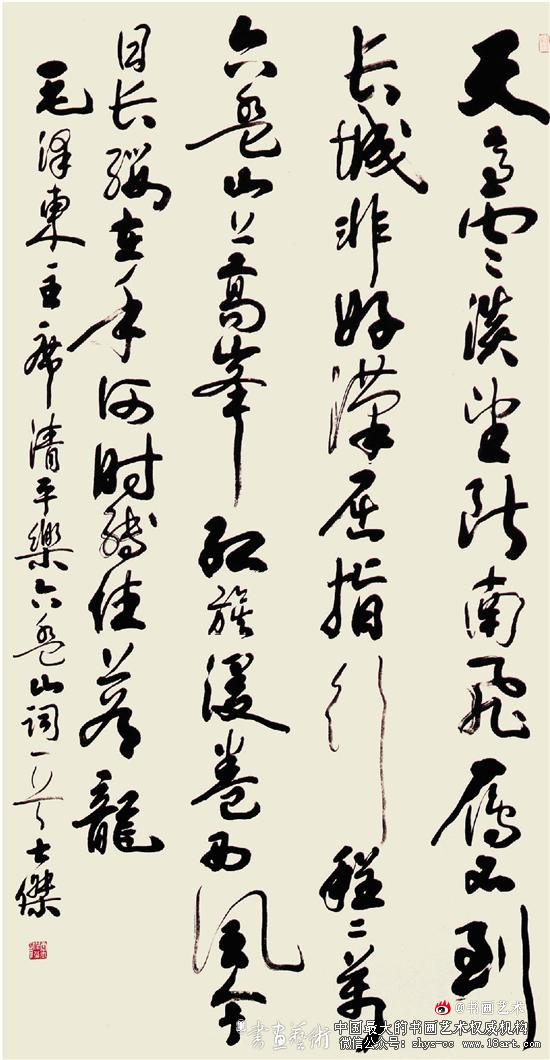
不明乎此,执拉斐尔的艺术为美,而斥毕加索的画为不美、为丑,执唐宋画家画为美,而斥明清文人画尤其是写意画为不美、为丑,这是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之,执毕加索的画为美,而斥拉斐尔的画为不美,执明清文人写意画为美、为雅,而斥唐宋画家画为不美、为俗,这还是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作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现实生活中对历代的、当世的楷模人物的宣传,类似于古典艺术。一个英雄人物,在宣传中总是被塑造得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瑕疵。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因此都有他的缺点。但我们把他塑造为大众学习的榜样,当然要关注并放大他的英雄事迹而忽略他的缺点,与真实拉开距离,唯有如此,才能弘扬高尚的精神。可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却要以“不真实”为借口挖出他的缺点并加以放大,质疑他的楷模性,抹黑他的英雄,这就颠覆了追求理想的正面精神标帜。
作为对生活丑陋的鞭挞,现实生活中对历代的、当世的反面人物的宣传,类似于现代艺术。一个奸佞人物,在宣传中总是被塑造成十恶不赦,没有丝毫优点。其实,砒霜也有它的治病救人之功,任何一个反面人物,也都是人而不是魔,因此都有他的优点。但我们把他塑造为社会公敌的典型,当然要关注并放大他的恶行而忽视他的优点,与真实拉开距离,唯有如此,才能鞭挞丑恶的现象。可是,一些别用心者却要以“不真实”为借口,挖出他的优点并加以放大,质疑他的反面性,平反他的耻辱,这就颠覆了摒弃丑恶的反面精神标帜。
新社会以审美来创造艺术美,莱辛的《拉奥孔》是古典艺术的理论基石。旧社会以审丑来创造艺术美,袁枚的《子不语》可作为现代艺术的理论开山。而无论审美还是审丑,一切艺术美包括写实的艺术美,都是与生活真实拉开距离的。不能以向生活真实的反面拉为“艺术与生活拉开了距离”,而向生活真实的正面拉为“艺术复制生活”、“客观再现”、“没有拉开距离”。生活真实经审美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而成为艺术美,是为生活美的理想。生活真实经审丑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而成为艺术美,是对生活丑的鞭挞。










